
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:http_imgload.jpg

被誉为“婺东第一村”的李坑,是婺源县秋口镇的一个小小村落。清晨六点,细雨霏霏,我在她的村外朝村里行走,满眼的油菜花,满山的新绿,村口的牌坊落在了身后。
溪流汩汩,水面上拥挤着一只只小船,阡陌上的耕牛淌过水田,石拱桥旁暗红的狮傩庙此刻也慢慢褪去雾霭,毗邻的店铺已有几家摊主在托举门板开始忙碌的一天。雨点淅淅沥沥地飘着,我躲在屋檐下看着商贩把里屋的工艺品一件件摆在门前的货板上,与店主闲聊之际,我挑拣了一件青花瓷烧制的手镯,算是答谢他的热情,又算是给自己此行留个纪念。
沿店家的指引进入村子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棵高大的樟树,据说已有几百年的历史,树的身后是一条石头的路面,蜿蜒着朝向村子,这就是李坑村,是李姓聚居的村落。清明的小雨若有若无,滴落在溪流里开着一朵朵透明的花,我站在小溪上的木桥上,望着两岸徽式的民居,白墙黛瓦在翘立的风火墙下参差错落,傍着穿村而过的小溪显出婉约的素颜。溪流的两岸拥挤着古朴的人家,保存完好的门额和泛着水光的门当诉说着前朝往事,门上镏光锃亮的铁环经年累月地敲击岁月的表面,门板上深深地烙上了圆圆的凹痕;打开一扇门,就是打开一扇尘封的时光。
亦儒亦商的新安商人,在东晋时代就已开始经商,先前主要以贩运米、盐、木、瓷土、生漆为主,后来发展到加工产品,即宣纸、砚台、笔墨、茶叶等;说到文房四宝,不能不提到歙砚,读大学时,有朋友数我一台椭圆的歙砚,说是用婺源龙尾山的歙石做成,砚台呈现蓝黑的细纹,这种螺纹砚研磨起来手感好极易出墨,涩不沾笔,滑不拒墨,用徽笔沾在宣州的画纸上书写自是一种享受。在李坑,出售砚台的铺子满街都是,品种已是琳琅满目。画国画与写书法的人,应该对艺术的发展做过贡献的徽商心存感谢。
徽帮不仅在封建时代创造了商业的奇迹,更在文化领域开拓了新的平台。有人告诉我,光在李坑村,自宋朝到清朝,村里先后走出了18位进士,七品以上官员有32人之多。北宋时期,本村就创建了“盘谷书院”;可见婺源人很早就很重视教育。
沿溪水往东走去,有一条窄窄的巷子仄入一户人家,墙壁挂着一块木牌,书有“李知诚故居”的字样,走进这位南宋武状元的老宅,首先看到的是中堂上高挂的红匾,“尚武堂”三个大字熠熠闪闪烁着金光,旁边黄色的灯笼写有“状元府”;一切家什布置极其简洁古朴,与其身份对比相去甚远。
由李知城故居后院走出,便可以看到山边一眼清泉,名曰“蕉泉”,泉井旁长着一丛丛芭蕉,听导游介绍:蕉泉曾是古时候人们求雨祭神的地方;二十多年前此地曾遭遇干旱,河水断流,仅凭此泉提供了全村人的生活用水。泉眼旁边是一条上山的路,它环绕村子的南边有一百多米远的距离,行至半山腰,一爿茶庄斜出山崖,店主殷勤邀我们四人绕几而坐,谈话中,获悉她从福建宁德远嫁此地,原来我们是在异乡邂逅老乡,她忙着烫杯沏茶,向我们介绍本地特产—婺源绿,尽管它名气逊于“黄山毛峰”,可在宋朝,婺源的谢源茶曾列为全国六种名茶的“绝品”之一 ,之后成为向朝廷进献的贡品。我们慢慢品着清悠的茶茗,望着无声的檐雨如柳絮儿飘,远处的青山雾气氤氲,篱笆尽处是隐约金黄的油菜花;──清茶最为风雅。我想起梁实秋的《喝茶》了。在这样的村落,这样的微雨,这样的空灵:“喝茶,喝好茶,往事如烟”。
除了好喝的还有好吃的,那就是木锤酥,这是当地有名的糕点,类似花生糖,只要你路过挂有木锤酥牌子的店铺,就能看到两个大汉抡锤夯着芝麻与糖与花生的稠状物,另一伙计把敲薄的饼糖再折叠成小方块,继续锤打,直到又脆又薄,香气四溢才算制作完毕。这一过程往往会吸引众多的游客驻足观看,那醇香会尾随你左右。
不一会儿,一路的油菜花就在我们脚下次第开放,白墙黛瓦的民居坐落在鹅黄的花丛里,湿漉漉的石路在阡陌围墙间蜿蜒,木板桥静静地卧在奔流的小溪上。紧挨着溪边有一堵照壁尤其显眼,这种照壁又称萧墙,在李坑村随处可见,看来是先人用此作为辟邪或挡风的需要,它们往往用青砖砌成,顶部用瓦片垒就,壁上中间或底部镶嵌着“福”字,寓意开门见福。我们所见的是清朝同治年间著名木商李书麟故居门前的照壁。在他旧居的左前方,隔着小溪建有一长列的走廊,跨过两米多长的石板桥,就进入了长廊的中间地带,它有两层翘檐,两头是一层长长的黛青色屋脊,长廊入口深处建有一戏台,在长廊与戏台间是空空的场地,能纳近千人,想必是当年族人在此观戏纳凉的去处;我坐在长廊的靠凳上俯看石阶下妇人在用溪水洗涤青菜和衣裳,流水的清澈让我羡慕眼前未被污染的环境,想起儿时在家乡的小河俯身掬水的样子,在这里,我仿佛回到逝去的岁月。
我停留在村子中心的申明亭,有三条小路交汇于此,两条小溪在此汇合亭子就处在路的中央,亭子为木架结构,四周通透,有12根柱子支撑,其中四根大柱作为受力的承重支柱,材质硕大坚实;三百多年来仍纹丝不动,想必现在已难觅到如此粗长的杉木。我见大柱两旁赫然挂着一幅楹联:
亭号申明就此聚议公断
台供演戏借它鉴古观今
从对联里不难看出申明亭自明朝末年落成以后,逢“每月望日、朔日,宗祠鸣锣聚众于此,批判和惩罚违反村规民约者”。当时村里出现的一切纠纷,如田产、婚姻、宅基、斗殴等,皆在这里进行调解和裁定;是明朝律法与乡规民约结合的进步产物。民风的严谨与质朴可见一斑。
申明亭的不远处,有一座著名的古居,叫“大夫第”。 建于清朝咸丰年间,屋主人李文进是一个五品的奉直大夫,他的官衔并非经过科举考试获得,实在是时势造就了他,作为一个茶叶的经销商,适逢清政府与太平天国的战事频仍,国库军饷匮缺,徽州官府由此鼓励商人捐钱以作军饷,其中捐献多的商人可以因此封官,李文进的五品官衔就是这样授封而来的。他的旧居是典型的徽式建筑,大门为石库门坊,门上是青砖门罩, 并有青瓦覆盖和戗角飞檐,精致的砖雕图案在门坊上显出岁月的沧桑。走进门里天井,正面的大堂上方挂着“春蔼堂”大匾,天光自上而下飘落,照着屋内的木雕,古代传说、琴棋书画通过木雕的表现惟妙惟肖。最妙的是二楼的回廊,据说是古代千金在此窥视求婚者的隐秘楼阁。在天井上方,四周的屋檐若有若无地滴着雨水,像在诉说当年的奢华。
毗连申明亭的水边,是五米多长的通济桥,为石拱造型,彩虹之状,桥身石阶有八级,站在拱桥上远眺,你会感叹小桥、流水、人家是如此奇妙的融合在一起:桥连着青石小路,路旁是错落有致的白墙青瓦的古典民居,民居连着女儿墙及雅致的漏窗,窗下是清澈的流水和欸乃的船橹,水尽处是一抹春意融融的绿树和远山……
近代婺源的商人在外发迹后往往回乡兴祠堂、盖私塾、拓祖宅,久而久之,李坑村的民宅逐渐形成统一的格局,典型的徽式建筑逃避了战火与文革的洗礼沿袭了下来,只要踏入她的巷道,面对簇拥的粉墙黛瓦、傲立的马头墙、水上的拱桥与船只、还有千年的古道、你会发出恍如隔世的喟叹。
我期待的阳光没有莅临,在春雨绵绵的巷子,最容易让人想起戴望舒的雨巷,空中的雨丝仿佛饱含水分的毛笔,淡淡地在我眼前晕染了一幅幅透明的水彩。也许是雨的衬托,让我感受了四月的水灵灵的娇媚。这被千年络绎的脚步轻轻敲醒的石路,这被雨点连绵弹奏的青砖瓦房,这被阳光之手抚摸的白墙,这被尘世遗忘的桃源胜景,时光是如何绕过她的裙裾,把她的青春留在了深锁的春闺。
当时间的河流向前奔流的时候,李坑──这只兰舟,一直停泊在时光之外。






 加好友
加好友  发短信
发短信

 Post By:2011/4/11 8:26:00
Post By:2011/4/11 8:26:00



 加好友
加好友  发短信
发短信

 Post By:2011/4/11 8:46:00
Post By:2011/4/11 8:46:00


 加好友
加好友  发短信
发短信

 Post By:2011/4/11 10:38:00
Post By:2011/4/11 10:38:00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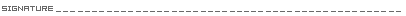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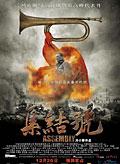
 加好友
加好友  发短信
发短信

 Post By:2011/4/11 11:30:00
Post By:2011/4/11 11:30:00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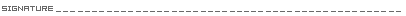


 加好友
加好友  发短信
发短信

 Post By:2011/4/11 12:30:00
Post By:2011/4/11 12:30:00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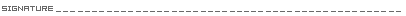



 加好友
加好友  发短信
发短信

 Post By:2011/4/11 16:13:00
Post By:2011/4/11 16:13:00



 加好友
加好友  发短信
发短信

 Post By:2011/4/11 20:53:00
Post By:2011/4/11 20:53:00


 加好友
加好友  发短信
发短信

 Post By:2011/4/11 21:05:00
Post By:2011/4/11 21:05:00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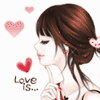
 加好友
加好友  发短信
发短信

 Post By:2011/4/11 21:47:00
Post By:2011/4/11 21:47:00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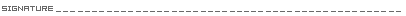


 加好友
加好友  发短信
发短信

 Post By:2011/4/12 10:21:00
Post By:2011/4/12 10:21:00
